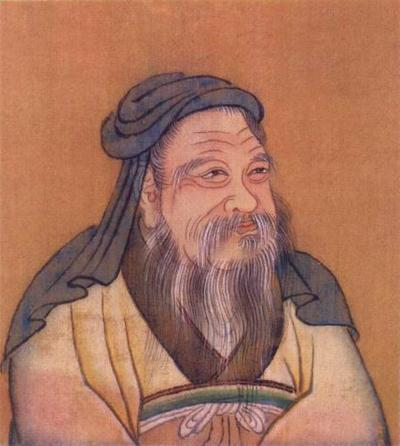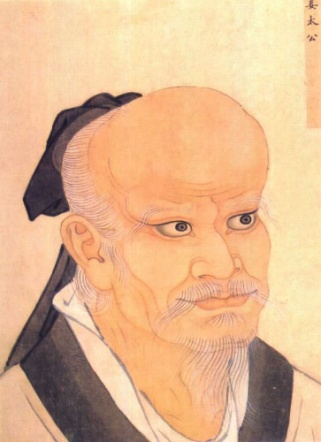文王被捕以后,家人和朝臣非常着急。
他们急忙找来了有莘氏的美女(估计是太姒夫人管娘家人要来的),骊戎的骏马,有熊国的九驷(三十六匹马加上战车),还有其他奇珍异宝。赶紧赶入商京,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献给了纣王。
这一下纣王倒被弄得不好意思起来,他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——姬昌何罪之有啊?于是不仅马上赦免了姬昌,检讨自己上了崇侯虎的当,并且把弓箭斧钺赐给文王,让他从此可以随意征伐不服从的邻国,不必再请朝命。
俗话说:“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”,自羑里脱归之后,文王姬昌的后福真是源源而至。
最大的后福是他遇到了一位绝顶的高人,并且拜为自己的太师——这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圣人、武成王姜子牙。
话说一向勤政的周西伯这天儿忽然感觉烦闷,非常想出去打猎。在打猎之前他卜了一卦,卜辞是:
将要得到的既不是龙也不是螭(无角龙),既不是虎也不是罴(一种熊),将要得到的是图霸称王的高级助手!
西伯大喜,立即出猎,果遇姜尚于渭水之南。
行家一伸手,就知道有没有。以文王这种三代圣王、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的能力,千年之内几乎不做第二人想,但与此人略一接谈,却感觉如同触电,几乎马上就要拜倒在地——哇塞,这儿老爷子可太厉害啦,简直就是一位活神仙下凡!其知识之渊博,见识之卓异,正是仰之弥高、钻之弥坚,瞻之在左、忽焉在右,如蛟龙之不可测,如沧海之不可极,如宇宙之不可穷!
估计文王姬昌当时高兴得几乎当场就要昏死过去,镇定了好久,他才说:我的爷爷太公早就预言:“将有圣人到周国来,周国将因此而一统天下”!今天您真的来了吗?真的是您吗?——我不是在做梦吧!我家太公已经盼望您好久好久啦!
当即把老先生请上车,回朝,立即拜为当朝太师(首相)和自己的私人老师,主管一切军政要务;号之曰:“太公望”——我爷爷企望中的圣人!
接着是派出豪华车队,从东海之滨某某城某某市(日照?)的棚户区,千里迢迢接来老先生的一大堆家眷,并立即与之连姻,让自己的太子姬发娶了老先生的小女儿邑姜,立为正妃。
这位姜尚姜子牙到底何许人也?
史册记载:此人乃东海(今之渤、黄、东三海)岸边人士,一介平民而已也。其先祖尝为四岳之一,因助大禹治水有功,封于吕地(南阳宛县)。他本姓姜氏,或从其封姓,所以又叫吕尚。
吕尚家早就破落了,家里很穷。他早年曾在殷都朝歌屠牛卖肉,黄河渡口孟津卖酒。据说也做过殷商的官员,可能是品秩太低的缘故,同朝为官的姬昌根本就不认识他。
关于他的早年和中年经历,还有很多种传说:什么算过卦、卖过米、种过地、打过猎、放过牛、捕过鱼、学过道等等等等,不一而足,也难稽考。
总而言之,这是商末的一位下层平民,虽有自由,却无资本。每日胼手胝足,沐风栉雨以求一饱。常常混的穷困潦倒,朝不保夕;往往漂泊不定,颠沛流离。
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,此人却没有悲观沉沦,而是逆流而上,孜孜不倦地学习、研究。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修,正当商周交接,天下将乱之际,终于蓄积起了惊人的能量——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雄才伟略、高瞻远瞩的潜在政治家、军事家。
正所谓:
“君子见机,达人知命;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?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!”
据专家考证:齐太公生于商王武乙时期,一生经历了商王武乙、文丁、帝乙、帝辛和周武王、周成王、周康王七代;曾服务于帝乙、帝辛、文、武、成、康六代帝君。
太公遭遇文王,应为公元前1056年(受命元年)或稍前。彼时太公70左右,文王60左右,武王40左右,太公小女邑姜20以下。
但何以武王晚婚若此,却又令人迷惑不解?莫非周人三十而娶,而恰值文王被拘,世子不怿,故而未婚?或者世子前此已有侧室,只是未育,故而史籍不传?
孔子曰:“太公勤身苦志,七十而遇文王”。
尉缭子说:“太公望年七十,屠牛朝歌,卖食盟津,过七十余主而不听,人人谓之狂夫。及遇文王,则提三万之众,一战而天下定”。
太公死时,已是周康王六年。《史记齐世家》:“盖太公之卒,百有余年”。或言其一百一十余岁方卒,也未可知!
如果我们把本次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暂时抛开,那么在近五万年的人类历史中,几乎有四万年是属于“先天时代”。
我们若以农牧业的出现为“文明”,则可把二者并称为“先天原始时代”。彼时统治人类的思想是“万物有灵论”,统帅各个氏族、部落的则是“酋长——巫师”。那是一个“民神杂糅,不可方物;夫人(人人)作享,家为巫史”的时代,所谓“人之初,天下通,人上通,旦上天,夕上天,旦有语,夕有语”。
许多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超能力直接交通上天,天神也常常下来,巡游省方。
农业文明开始以后,人类的私欲日增,先天能力渐渐减弱。高级生命也很少下顾,于是颛顼下令“绝地天通”的神话就诞生了——“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,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”。
人和神之间拉开了距离,但仍然是以神为主,以神为本,属于“神本主义”文化。
“神本主义”文化的最高峰,就在殷商。
正如《礼记》所说: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礼”。
史料和考古发现证实:
殷人好卜:殷商从上到下,事无巨细,先卜而后行。可以说是无日不卜,无事不占,极端宿命论的思想笼罩着一切;
殷人惧祟:日常起居,禁忌极多。简直是四处闹鬼,无处不祟,举手投足,动辄得咎,把自己搞得几乎精神分裂;
殷人好祭祀:祭祀之频繁,花样之繁多足以使现代人崩溃。祭典上杀羊杀牛杀狗杀人。凡有大事,如祭神祭祖,求雨求年求祛疾求长寿,乃至新居落成,陵寝告竣,必杀人以登闻;
殷人好杀殉:诸侯与商王一级杀殉,少则数十,多则数百。一些是近臣姬妾,但大部分是抓来的奴隶。有青年男子,也有妇女和儿童。其杀戮方式:砍头、活埋、宰割、焚烧不一而足,真是惊心动魄,令人发指!
晚期的上层殷人,已经堕落为一个“咆哮于中国,敛怨以为德”的野兽种族。他们“有虔秉钺,如火烈烈”四出征伐,把无数的苦难倾倒给周边的方国部落,倾倒给数十百万无辜的人民!
如何处理“天人关系”是古今思想界一大难题——在这个问题上,无论你倾向于以神为本,还是倾向于以人为本,其实最终都应该追求一种平衡,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、科学的信仰,极端倾向绝不可取。
有神论的确是正确的,也是完全可以证明的(主要用禅定中开发出来的各种功能),但由此走向极端也会变成迷信,变成对高级生命赤裸裸的侮辱。
象美洲的阿兹特克人,每年杀人数千,日以杀殉娱神;
象中世纪的欧洲教会,大搞宗教裁判所,到处搜杀女巫;
或者象现代的宗教极端分子,鼓吹杀戮平民,也能进入天园。
这不是肆意妄为是什么?等待他们的是地狱。
道德崇高的高级生命,岂会喜欢这种货色!
以人为本的立场更正确一些——但发展到极端也会变成邪说、邪教。
譬如,达尔文的演化论,胡说人类起源于猿猴,就是一种邪说;而那种在毫无深入研究的情形下,断然否定高级生命的存在,断然否定灵魂的存在,断然否定永恒道德的存在,整天鼓吹阶级斗争、阶级专政、暴力革命的思想体系应该叫什么,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。
这是一种可怕的学说,仿佛瘟疫,曾经毁灭许多国家,迄今还在使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、败坏。
总之:
神本的极端是抹杀人,一切为了神,人变得可有可无;
人本的极端则是抹杀神,斩断了自己的根,斩断了自己的神圣来源,把自己等同于动物,人同样会变得轻如鸿毛,贱如草芥!
在神本主义时代,理性的光芒也会不时闪烁。譬如商初的伊尹就经常说:
“惟上帝不常,作善降之百祥,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
“惟天无亲,克敬惟亲;民罔常怀,怀于有仁。”
“天难谌(相信),命靡常;常厥德,保厥位。”
“非天私我有商,惟天佑于一德;非商求于下民,惟民归于一德。”——诸如此类。
但睿智的贤圣终归是少数,蒙昧主义最终必定会卷土重来,占据优势,它集中表现在殷商末王子受辛的名言:——“呜呼,我不有命在天?”
高踞在大邑商宝座上的旧天子们深信自己“有命在天”,“荷天之宠”;潜伏在暗处,正准备战胜攻取、取而代之的新天子和群臣们却深信: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。
在在下看来:周初人们天命观之纯正,实非前后世代之所能及:
“皇矣上帝,临下有赫;监观四方,求民之莫(瘼)。”
光明伟大的上帝,象太阳一样照临着下土;他监察着天下四方,关心着人民的疾苦。
“天监在下,有命既集。”
——上天监视着下方,天命已经属于文王。
“天监有周,昭假于下。”
“无曰高高在上,陟降厥士,日监在兹。”
“天乃大命文王,殪戎殷,诞受天命。”
“有命自天,命此文王,笃生武王,保右(佑)命尔,燮伐大商。”
“昊天有成命,二后(文王、武王)受之。”
“明昭上帝,迄用康年。”
“我其夙夜,畏天之威,于时保之。”
“时迈(按时巡视)其邦,昊天其子之。”
“上帝是依,无灾无害。”
……
等等等等,不胜枚举。
正如伟大的屈原所说:“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;夫维圣哲以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”。
图/周文王 像
在周初的四位巨人中,文王的政治思想因西晋永嘉之乱,今、古文《尚书》相继散佚,保存下来的很少,但其“敬天”、“明德”、“慎罚”以“怀保小民”的主题思想十分清晰。
在政治实践上,文王作为人君先“立仁于己”——“古之政,爱人为大”(孔子),“治世莫若爱民”(宋·王昭素);然后躬行仁政:敬老,尊齿,乐施,亲贤,好德,恶贪,谦让(七教也),使得境内:“大夫忠而士信,民敦俗朴,男悫而女贞”,境外:“来远怀众,仁名远播”,天下之民归之若流水,连很多奴隶都逃过来了,以至文王不得不颁布“有亡荒阅”的法令。
“划地为牢”,“泽及枯骨”的爱民故事,流传至今!
文王深明天道,深谙宇宙的辩证运动。以下《易经》的卦爻辞足以说明这一点:
“潜龙勿用”;
“亢龙有悔”;
“大人虎变”;
“君子豹变”;
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”;
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;
“有孚光亨,利涉大川”;
“自天佑之,吉无不利”;
“井渫不食,为我心恻”;
(不能把握时机也)“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,厉无咎”;
(有备无患)“劳谦君子,有终吉”。
在新发现的《保训》中,文王谆谆告诫嗣王,要:“自稽厥志(自我省察),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(不要违背老百姓的愿望),厥有施于上下远迩(才能普济万民)”。
告诉武王,古昔圣王的施政秘要就是一个“中”字,要“建中于民”,要以中道治国。
灭商之后武王真的也要“归中于河”——迁都于黄河中游,“莅中国而抚四夷”,是不是受了文王的暗示呢?
图/周武王 像
武王姬发作为思想者显然不及文王、周公和太公三位来的声名显赫。但他的思想非常明澈:
“惟人万物之灵;”
“天矜(怜悯)于民,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;”
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,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;”
“惟天阴骘(保护)下民,相协厥居;”(使他们和睦相处)
“吉人为善,惟日不足;”
“虽有周亲,(至亲)不如仁人;”
“亶(诚实)聪明,作元后,(天子)元后作民父母;”
“惟天惠民,惟辟(君主)奉天;”(以安民也)
“抚我则后,虐我则仇。”——抚育我才是我的君主,虐待我就是我的敌人。
——民本主义的立场何等鲜明!
王国维先生曾说: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,莫剧于殷周之际。”
概而言之,这就是一次从“神本”到“人本”的急剧转变。在这一转变中,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公姬旦。
图/周公旦 像
这是一位让我们的“至圣先师”孔夫子拳拳服膺的伟大历史人物,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——儒家尊之为“元圣”。
如果说,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,那么在两千年的三代封建社会中,周公旦就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奠基人。没有周公,儒家简直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“百家争鸣”似乎也无从谈起。因此汉唐以降,明清之前,历朝都是“周孔”并称——魏晋之际的嵇康就是因为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而被诛杀。
东征之后,周公第二次大分封,制礼作乐,不仅开启了有周八百年璀璨辉煌、仪态万方的礼乐文明,并且为嗣后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调。
我国上古文献遗存甚少,而在《尚书》和《逸周书》中,有关周公的记载是最多的;在诸子百家的追述中,周公也往往在唱主角。
旧说《周礼》(周官)《仪礼》两书为周公所作,谓之“周公致太平之迹”,“非圣贤不能作”,太史公司马迁就持此说。
近人则痛诋之,以为文辞不类,不够诘屈聱牙,必是战国时人伪托。他们显然忘记了,司马迁本人就经常改写古文,把它改换成通俗的汉代口语。战国诸子这样做,又有什么不可以呢?古代“非天子,不议礼,不制度,不考文”,普通人又怎么会擅自写出这样两本书来,且又如此的精详周密、和谐典雅?
《周礼》和阐释它的《礼记》:“经国家,定社稷,序民人,利后嗣”,“吉凶军宾嘉”五礼兼具,影响深远,直迄清末,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制度纲领。
孝悌仁爱、温文敦厚是周公的天性——“旦为子孝,笃仁,异于群子”。(《史记》)他把自己宽裕温柔的个性,把周人浓郁的血缘亲情贯注在周礼中。“善继人之志”,“成文武之德”,提倡“以德治国”、“以礼治国”——“祀德纯礼,明元无二”。缔造了西周这个令孔子和后儒推崇备至的理想社会,把中国第一个文明时代(三代)推向了巅峰——自己也成了儒家最高的人格典范。
周公“明德慎罚,不敢侮鳏寡”,其论列九德:“孝、悌、慈惠、忠恕、中正、恭逊、宽弘、温直、兼武(明刑)”——法治乃其末也,并非今人所说“德法并重”。故后世汉宣帝刘询以:“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?”抢白太子。
周公的思想博厚高明,兹举数例,可见一斑:
“人无于水监(鉴),当于民监(鉴)。”
“若保赤子,唯民其康乂(康乐安定)。”
“民情大可见,小人(小民)难保。”
“民心无常,惟惠之怀。”
“以德配天”,“敬德保民”。
“与民利者,仁也;为民犯难者,武也。”
“王欲求天下民,社设其利,而民自至。”
“德以抚众,众和乃同。”
“维明德无佚(失也),佚不可还(失去就找不回来)。”
“肆惟王其疾敬德(现在王要加紧推行德政),王其德之用,祈天永命(王该用美德去向上帝祈求长久的国运)。”
“惟命不于常(天命无常),汝念哉(你要小心啊)!”
殷商“唯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。”
“天非虐(并非上天虐待下民),惟民自速辜(是人的罪恶引来了灾难)。”
罚过:“父子兄弟,罪不相及。”
周公深得文王真传,追述其父:
“惟文王之敬忌,乃裕民。”
“克明德慎罚,闻于上帝,帝休,天乃大命文王。”
“维文考恪勤战战,何敬、何好、何恶?时不敬,殆哉!”
“在昔文考,躬修五典(五常之教),勉兹九功(慎不可犯的九种过错,如:淫巧破制,荒乐无别等等),敬人畏天。”
周公行政:“老弱疾病,孤子寡独,惟政所先。”
“乡立巫医,具百药,以备疾灾。”
“称贤使能,官有材而士归之。”
“关市平,商贾归之。”
“分地薄敛,农民归之。”
周初三圣之树立,正如《中庸》所赞:“大哉,圣人之道,洋洋乎发育万物,峻极于天!”
对于我所说的道家高人卜卦,眼前会出现图像,很多人表示怀疑。那么请参考科学奇才尼古拉·特斯拉的经历:
“如果有人对我说出一个词,那么这个词所示意的物体的景像,便在我的眼前生动地浮现出来,有时候我都无法分清,究竟我看到的是否真有其事。这使我万分难受和焦急。我请教那些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的研究人员,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令我满意地解释清楚这种现象……”
特斯拉推论,这些景像并不是幻觉。每当夜阑人静之时,他曾见到过的丧葬或者别的叫人心悸的情景,便在他眼前活灵活现地涌现出来,如果他把手伸过去,这种景像也还是留在空间里纹丝不动。
——道家真人的功力更加强大,所以图像全是活动的。
古语说的好: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”。
文王姬昌的长处在于知天道、擅政经,但在军事上和谋略上则相对短板。本来嘛,天性如此仁厚的一个人,你让他整天研究怎么杀人,怎么颠覆敌国,他肯定不会十分在行。
我们之所以后来也把他尊为军事家,是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生猛的军事天才——吕望。
图/吕望(姜尚)像
吕望在当时和后世都十分牛叉,后世的儒、法、道、兵、阴阳、纵横甚至经济学家一致尊奉他,号称“百家宗师”。
实践表明,这确实是一位“文能安邦,武能定国”的旷世奇才,全智全能,正如刘备得诸葛而分三国——“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。”
姜太公留下或者托名于他的著作很多。
在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中,李靖说:太公的谋略有八十一篇,不可以言穷其意;太公的言论有七十一篇,不可以兵穷其妙;太公的兵法有八十五篇,不可以财穷其用。谋、言、兵共二百三十七篇,构成所谓“三门”。
“张良所学,太公六韬三略是也。”
兵法最早出现在黄帝时代,“周之始兴,则太公实缮其法。始于岐都,以建井亩,以立军制,以教战法。”“周司马法,本太公者也。太公既没,齐人得其遗法。至桓公霸天下,任管仲,复修太公法,谓之节制之师,诸侯毕服。”
——以此观之,今日之《武经七书》中,三略、六韬都是太公所遗,司马法中也保存着太公的部分思想。
战国武学,齐国最盛,孙子和孙膑显然受到太公极大的影响。吴起的老家卫国左氏邑在山东曹县,战国魏人尉缭相传是鬼谷子的高足,而鬼谷先生正是齐人。
游说失败,苏秦从自己家箱子底下翻出来的“周书《阴符》”,估计也是太公的遗作。
我们当然不是说,现存的《六韬》和《太公兵法》、《太公金匮》、《太公阴谋》残篇等等都是太公本人的手笔,而是说这些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。他的思想在西、东两周是如此著名、如此权威,广为人知,相信很难有人敢去伪造。
综合所有遗编,太公的思想可以简括如下:
一、存心:“敬胜怠者吉,义胜欲者昌;日甚一日,寿终无殃。”
“福生于微,祸生于忽;慎始与终,完如金城。”
“人莫踬于山,而踬于垤。”——人没有被大山绊倒的,绊倒人的都是小土堆。
“荧荧不灭,炎炎奈何?涓涓不塞,将成江河;绵绵不决,或成网罗;青青不伐,将寻斧柯。”
二、立政: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,乃天下人之天下。”
“同天下之利者,则得天下;擅天下之利者,则失天下。”
仁义道德之所在,天下归之。
治国必以爱民为本。要“爱民”、“顺民”、“贵民”。
圣帝明王,自己粗衣恶食,以存养百姓。“驭民如父母之爱子,如兄之爱弟,见其饥寒则为之忧,见其劳苦则为之悲;赏罚如加于身,赋敛如取于己。”故
姓“戴之如日月,亲之如父母。”
要“敬其众,和其亲(宗族),敬其众则合,和其亲则喜,是谓仁义之纪。”
“与众同好靡不成,与众同恶靡不倾。”
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,顺民心而治理(这个周公有异议)。
三、尚贤:“君子乐得其志,小人乐得其事”,所以要“举贤而上功”。
“以饵取鱼,鱼可杀,以禄取人,人可竭。”
对于贤士要“按名督实,选才考能”,使之名副其实。
决策要集思广益,充分发扬民主:“以天下之目视,则无不见;以天下之耳听,则无不闻;以天下之心虑,则无不知”。
显而易见,姜太公最突出的还是他的军事才能,要不怎么能立马当上三军总司令呢!
他的军事思想全面、深刻而精辟。
如果说《孙子》比较强调兵者诡道,比较强调智胜、兵胜,那么太公兵法则更加注重实力,更加注重仁胜、政胜。在这一点上,他更加接近吴起和商鞅(“凡战必本于政胜”;“兵起而程敌,政不若者勿与战”),与近代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也相当一致。
太公兵法,可以说是一种阳性兵法,其来源我们最后再说。
论兵:“非德不昌,非兵不强。”治军必先经国,言兵必以政治为先,要“安不忘危,存不忘亡”。
强调“天人合发”——“天道无殃,不可先倡;人道无灾,不可先谋”,“必见天殃,观人灾,乃可以谋”,但“时至不行,反受其殃;天与不取,反受其咎”。——后代的革命家们真该向古人多多学习啊!
用兵的最高境界是“大兵无创,以全胜无斗争于天下”。
治军: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将领:“得贤将者,兵强国昌;不得贤将者,兵弱国亡。”
要以五材选将: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
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共苦:“冬不服裘,夏不操扇,雨不张盖。”炊者皆熟,将乃就食;劳者皆息,将乃就寝。这样才能打造出天下无敌的“父子之兵”,才能“战如风发,攻如河决”!
“军中之事,不闻君命,皆由将出。临敌决战,无有二心。”
要以各种人才组成七十二人的参谋机关,各有分工,各司其职。
用人要“崇礼而重禄——崇礼则智士至,重禄则义士死。”“万人必死,横行天下。”
执行军法则“杀贵大,而赏贵小。”法不阿贵,赏不遗细——军法面前,人人平等。
攻伐:“密察敌人之机,而速乘其利,复疾击其所不意。”
“变生于两阵之间,奇正发于无穷之源”,所以必须随机应变,要“见胜则起,不胜则止”。
“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,三军之灾,莫过狐疑”。
“巧者一决而不犹豫,是以疾雷不及掩耳,迅电不及瞑目”。
进攻要“赴之若惊,用之若狂;当之者破,近之者亡”。
具体的用兵方略、战法很多,什么山地战,泽地战,林地战,火地战;怎样用骑,用步,用车等等,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武攻之外,尚有文伐十二法,确实比较阴损。乃是用奉承、贿赂、收买、离间、利诱等手段促使敌人骄狂自大,耽于逸乐,上下离心,内外解体。什么:“淫之以色,啖之以利,养之以味,娱之以乐”等等等等,一句话:——“多方以误之。”
太公能预测,会望气,他说:“凡兴师动众,陈兵,天必见其云气,示之以安危,故胜败可逆知也。”
“凡攻城围邑,城之气色如死灰,城可屠;城之气出而北,城可克;城之气出而西,城可降。”
“三军齐整,金铎之声扬以清,鼙鼓之声宛以鸣,此得神明之助,大胜之徵也。”
——这种用兵境界早已超出了凡人,看起来《封神演义》的故事也并不都是空穴来风!
战胜之后,以道家无为之术,休兵养民:“天无为而成事,民无与而自富。”——千万不要瞎折腾。
姜尚最超前的地方,还是他的经济理论。
他认为政治应该先于军事,而经济又应该先于政治。
衡量一个君主是不是合格,是不是优秀,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能不能把人民生活提高上来——“故人君必从事于富,不富无以为仁。”
富国的关键在于“大农、大工、大商”——农工商并尊,谓之“三宝”。国无食不存,国无器不富,国无商不活,显而易见。
姜太公主张专业分工:“农一其乡则谷足,工一其乡则器足,商一其乡则货足”,要“通商工之业,便鱼盐之利”,本末并举。
他为大周朝尤其是他亲自治理下的齐国,建立起了完备的经济制度,核心是——“九府圜法”。
什么叫“九府圜(yuán,钱币)法”?
《周官》的解释是:“泉府、大府、王府、内府、外府、天府、职内、职金、职币”为天子九府。其职能是用行政手段,令钱币与布帛实物不断流通,使之聚散适宜,既无积滞,也无匮乏,务期富国裕民。
简而言之,这是一种建立甚早的国家经济机关,实行着一种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财政货币政策。
这是不是跟“商人”学习的结果?我们不得而知。
《汉书·食货志》追述: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,黄金方寸重一斤,钱圆函方(圜又有圆义,函乃内孔),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,长四丈为匹。故货宝于金(以金为宝),利于刀(刀币收藏便利),流于泉(用钱来流通),布于布(用布分配),束于帛(用帛聚存)。
——这些对金钱布帛的规格、形制、计量、比价的规定,大大方便了交换与流通。
太公要求敛散以时,轻重有节,平抑物价,调剂余缺。以开源节流来防止“上溢下漏”。从而保证了两周的经济繁荣。
就国于齐之后,太公大力发展经济。
农业:田野辟,六畜旺,作物甚多,盛产禾麦。民人安居。
工业:多种工业发达,尤以冶铸和舟车制造著称(轮扁为齐巧匠)。最值得一提的是:齐国的丝织业极其有名(新裂齐纨素,皎洁如霜雪)。史称太公劝其女工,极其技巧而齐“冠带衣履天下”。后世汉人开辟丝绸之路,产品远销东南亚、印度、罗马帝国,其大部分丝织品依然出自齐地。
商业:天下人物归之,如水之就海,“繦(用绳子穿好的钱串)至而辐辏”,“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”。齐都临淄也成了六国中首屈一指的大都会,如今日之巴黎、纽约,为世人所艳羡。
齐国政治开明、经济发展、学术繁荣,很快就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最发达地区。
“以太公之圣,建国本”,真可谓硕果累累!
太公既遇文王,则天下形势陡变,套用李太白的一句话,叫做:
鱼水一唔合,风云四海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