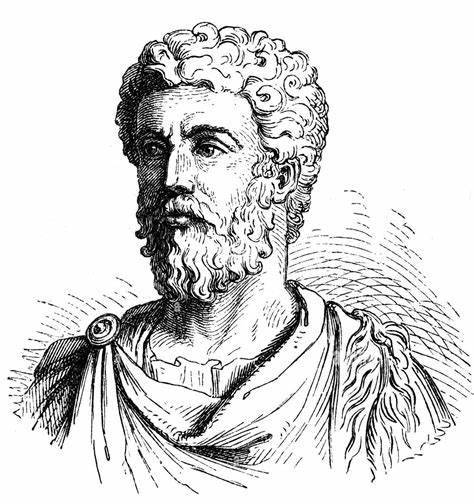斯多葛哲学的最后一位主要代表是马可·奥勒留。
在公元96年至180年间统治罗马帝国的有五位杰出君主(五贤帝),他们分别为:
涅尔瓦(Nerva,96年 - 98年,外号“仁帝”),
图拉真(Trajan,98年 - 117年,外号“勇帝”),
哈德良(Hadrian,117年 - 138年,外号“智帝”),
安敦尼(Antoninus Pius,138年 - 161年,忠帝),
最末一位就是马可·奥勒留(Marcus Aurelius,又译马可·奥里略,161年 - 180年,外号“哲帝”,哲学家皇帝)。
这五位皇帝仁慈聪睿,勤政爱民,刚柔相济;在位年间政治清明,依法治国,境土四拓,把伟大的罗马帝国推向了最强盛的巅峰,使帝国在法律制度、道路交通、度量衡、货币等许多方面都获得了统一。
爱德华·吉本在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中,把这段时期称赞为“人类最幸福的年代”,歌颂备至。
安敦尼·毕尤(生于公元86年9月19日,死于161年3月7日,享年74岁),是罗马帝国的第十五任皇帝,公元138年 - 161年在位,《后汉书》称之为大秦王安敦。
哈德良皇帝认养安敦宁·毕尤为嗣子的附加条件,是安敦尼同等认养维鲁斯和奥勒留两人(安敦尼皇帝也是奥勒留的姑父,姑父无子,便以奥勒留为养子,所以马可·奥勒留的全名是马可·奥勒留·安敦尼),所以奥勒留属于是被隔代指定的帝国继承者。
奥勒留于公元121年4月26日生于罗马,原名马可·阿尼厄斯·维勒斯。
他父亲一族先世曾是西班牙人,但已定居罗马多年,并从韦帕芗皇帝那里获得了贵族身份(我们说过,韦帕芗统治时期曾授予许多外省贵族罗马公民权,使各地贵族能广泛参政)。母亲一系也是地位显赫的贵族,其外曾祖父卡提留斯·西维勒斯曾两次担任执政官。可以说,其父母两方都是世代簪缨,钟鸣鼎食之家。
奥勒留尚在襁褓时其父阿尼厄斯·维勒斯就死在了执政官任上,他的母亲和祖父把他抚养长大,他的童年是相当幸福的。他的祖父曾三度担任罗马的执政官,一次在图密善皇帝时,两次是在公元121至126年间(即奥勒留的幼年)。
他在很小的时候,因为性格真诚、坦率,已经被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德良注意到,因而受到了特殊的教育。
他六岁获骑士衔。七岁入学于罗马的萨利圣学院,在希腊文学、拉丁文学、修辞、哲学、法律、绘画等方面,得到了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。
他的老师中,戴奥吉纳图斯,朱利乌斯·拉斯蒂克斯(后来曾两次被奥勒留任命为执政官),阿珀洛尼厄斯(被安敦尼专门请到罗马来教奥勒留),塞克斯都(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孙子),克特勒斯,克劳迪厄斯·马克西默斯都是斯多葛派哲学家。——他起初也曾像当时大多数罗马青年一样热衷写诗,但后来放弃了文学,专心于斯多葛派哲学。
作为储君,他自然也要接受王室继承人的训练,学习军事科学和指挥技艺。
129年,他8岁时,曾为古罗马战神祭司。
马可·奥勒留自幼便模仿希腊与罗马的哲学家们,生活朴素,艰苦自持。虽然体质羸弱,却勇气过人。
公元138年,17岁时,哈德良皇帝去世,养父安敦尼继位为帝。
公元139年,18岁时,奥勒留即已获得“恺撒”称号,协助养父兼姑父治理国家。第二年更被擢升为执政官。
145年,24岁时,奥勒留结婚,再次被推举为执政官。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个,即康茂德长大成人。
公元 147年,26岁时,奥勒留担任了护民官。
公元 161年,他40岁时,养父安敦尼皇帝去世,奥勒留在161年3月7日与其弟卢修斯·维鲁斯(他们同一个养父)一同继承了皇位。
这是罗马帝国首度出现两帝共治,不过国政在多数时候都由奥勒留定夺。
卢修斯·维鲁斯(161 - 169年在位)还娶了奥勒留的女儿路西拉为妻,所以,奥勒留不仅是维鲁斯的兄长,还是他的岳父。
据说,元老院曾要求奥勒留一人独自执掌朝政,但是奥勒留却坚持要两人共同在位。维鲁斯虽然才华不及奥勒留,却有自知之明,对奥勒留敬重有加。
公元 162年,奥勒留41岁时,维鲁斯统兵征讨东方的叛乱,经过四年苦战取得成功,击退了非常难缠的帕提亚人(帕提亚轻骑兵弓马娴熟,战斗力很强)。
是年台伯河发生洪水,国内疾病蔓延,财政拮据,奥勒留卖掉了皇冠上的珠宝以筹集军饷、进行赈灾。
166年,45岁时,奥勒留派遣使者经日南(汉郡,汉武帝时设立,在今越南中部,东汉末以后,为林邑国所有),给东汉皇帝送来象牙、犀角、玳瑁,与中国建立了通商关系。
公元169年,维鲁斯去世,奥勒留开始独自治理国家,并亲征北疆平定叛乱。
在与日尔曼人的战争中,奥勒留曾经在位于多瑙河畔的卡尔嫩图穆要塞长住了三年,在这期间他将马可曼尼人(日耳曼部落的一支)完全赶出了潘诺尼亚,几乎将他们全歼。
公元 174年,53岁时,他率兵与日耳曼人作战,取得了针对夸迪部落的重大胜利。
公元 175年,东部诸省总督阿维第厄斯·卡希厄斯在叙利亚举兵反叛,自立为帝,旋即被部下所杀。奥勒留亲至东方,赦其遗族。行军途中,妻子去世,使奥勒留陷入悲痛之中。
公元176年,55岁时,奥勒留从东方归还,随即奔赴日耳曼前线,所向皆克,在罗马举行了凯旋式。
公元177年,其子康茂德获得“奥古斯都”称号。一些基督徒因为坚持信仰在里昂被杀。
公元 179年,奥勒留再次统兵大败日耳曼部落,但在这次战役中他也感染了传染病。
180年3月17日,奥勒留59岁,在位于下潘诺尼亚的多瑙河边的希尔米乌姆军营中病逝。遗体或骨灰被运回罗马,在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他被人们当做神一样地崇敬。
图/马可·奥勒留在前线
奥勒留骑马铜像是公元二世纪罗马的代表作品,中世纪基督徒曾误以为是君士坦丁皇帝。
众所周知,马可·奥勒留的思想集中在《沉思录》(The Meditations by Marcus Aurelius)一书中。
大概是事关气运,在他在位的近二十年间(公元161 - 180年),罗马帝国不断遭遇台风、地震、瘟疫等自然灾害,边阃狼烟四起,内部也偶有叛乱。他呆在首都的时间有限,许多时候都是在率军远征或者驻扎前线。在东荡西除,戎马倥偬的岁月里,在冲风冒雪,夙兴夜寐的军旅生活和征战途中,奥勒留撰写了十二卷心灵独白,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,后人名之为《沉思录》。
《沉思录》译本很多,译文质量明显地参差不齐。有一些显然特意做了曲解,甚至是删节,以适应某种意识形态(譬如梁实秋译本第六卷13节:“这紫袍不过是在蚬血里染过的羊毛;所谓性交,亦不过是体内的消耗和一阵阵的分泌黏液而已”,有些大陆译本就径直删除了)。
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,在下在不同的译本中摘录了一些隽永的警句、名言,以便没有时间看《沉思录》的网友对马可·奥勒留的思想可以略窥一斑。如:
“从我的母亲我学习了敬畏上帝,慷慨;不仅是不肯为恶,甚至不起为恶的念头(这是梁实秋译的,仿佛刘备的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)。
“无论什么事情对你发生,都是在整个万古永恒中就为你预备好的,因果的织机在万古永恒中织着你和与你相关联的事物的线”。
希腊人把神灵为人的一生编程比作女人纺织,蛮形象的。斯多葛哲学非常接近宗教,他们相信宇宙中有神,神话传说乃是寓言。人的灵魂来自神,所谓“至善”就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天神合作。他们是宿命论者,认为命运不可改变,人所能改变的,只是自己的内心,或者说:自己对事物的看法。
“若是你不同时参照神的事物,就不会把有关人的所有事情做好,反之亦然”。
十分正确,见多才能识广,参照神的事物就是取法乎上。
“…神的确是有的,并且他们是管人间事的;他们已经赋予人类以力量,令他不致堕入邪恶”。
对于邪恶之徒,神的存在十分可怕。他们汲汲于否定神灵,掩耳盗铃,唯恐在地狱中遭到惨报。
“凡是由神那里来的必是极好的,值得我们尊敬;从人类那里来的,值得我们爱,或者值得我们同情”(他的意思,也包括灾祸)。
“只可在一件事上取得快乐与安息——行善又行善,全心地想念着神”。
凡是这样直截了当谈论神和上帝的,多半是梁实秋的译文。大陆的一些叫兽,倾向于把有没有神,弄得晦暗不明。
“你一向是怎样对待神、父母、兄弟、妻室、子女、教师、导师、朋友、亲戚、家人?你敢说直到今天为止对待他们实实在在的是‘没做过一件错事,没说过一句错话’吗?”
“在终局未到之前,该怎么办呢?除了敬礼天神,赞美天神,对人行善,容忍别人并且克制自己,还要常久记住:凡是这肉体的人生的以外的一切事物皆不属于自己,皆非自己所能控制,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为的呢?”已经非常像基督徒。
“面向不朽的神将使我们欢愉”。
“一个有力者必须仅仅做神灵将赞赏的事情,接受神给他的所有东西”。
“那从地里生长的东西要回到地里,而那从神圣的种子诞生的,也将回到天国”。
他相信灵魂将回归天国,因为人分有神的圣火。
“有些人问:你在哪儿见过神?或你怎么知道他们存在并如此崇拜他们呢?
对于他们,我回答说,首先,他们甚至可以用肉眼看见;其次,我甚至没见过我自己的灵魂,但还是尊重它。那么对于神,我是从我对他们力量的不断体验中领悟到他们存在并崇拜他们的”。
确定有神论最正确的方式还是修炼,打开天眼,把自己的视域扩张到可见光以外,亲眼目睹神灵们的所作所为。
“这怎么可能呢,对人类仁慈的神灵在把所有事物安排好之后,单单忽视了这一件事:即某些很好的人,我们可以说,某些与神意最相通的人,通过他们虔诚的行为和严格的服从而与神意最亲近的人,当他们一旦辞世,却绝不会再存在,而是完全地消失?”
由于缺少天启的引领,奥勒留对死后的轮回(如柏拉图所谈),并不十分确定。他曾疑惑道:“如果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,那么自古及今,天空以怎样的方式为他们腾出地方来呢?”——他虽然经常谈到造物主,但似乎还没有上帝统摄一切、至高无上、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非常明确的概念。
奥勒留是一个世界主义者,一个宇宙公民,是我们的前辈和楷模;他胸襟博大,似可吞吐天地。
他说:
“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,不过是宇宙的一角;整个的海洋不过是宇宙的点滴,阿陀斯山(希腊名山,海拔6350英尺,1英尺=0.3048米)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泥土;现在不过是永恒中的一点;一切事物都渺小得很,这样容易改变,这样容易消灭。”
“就我是安东尼来说,我的城市与国家是罗马;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,我的国家就是这个世界”。
“那不知道世界是什么的人,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。那不知道世界为什么目的而存在的人,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”。
至理名言,不了解全体,你就不能清楚地了解部分——因为你没有参照系。
“最能培养高尚胸襟的事,莫过于对人生遭遇的一切,作确实而有条理的研究,从而参究这宇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?……它能引发我的什么美德?诸如谦逊、勇敢、真实、忠诚、无欺、自足等等。”
对人生遭际作有条理的研究,就是哲学的起源。奥勒留非常重视真诚,就像《中庸》所说:“故至诚无息,不息则久,久则征,征则悠远,悠远则博厚,博厚则高明”。
“这是柏拉图的一个很好的说法:谈论人们的人,也应当以仿佛是从某个更高的地方俯视的方式来观察世事,应当从人们的聚集、军事、农业劳动、婚姻、谈判、生死、法庭的吵闹、不毛之地、各种野蛮民族、饮宴、哀恸、市场、各种事情的混合和各个国家的有秩序的联合来看待他们”。
俯瞰是最好的观察方式,可以洞隐烛微、一览无余。
作为斯多葛主义者,马可·奥勒留极端推崇理性。他说:“如果你做事能遵从正确的理性,诚恳、勇敢、从容,专心一意,保持内心的纯洁神圣,好像现在立刻就要把它奉还给造物主一般……那么你的一生将是幸福的”。
“要尊重你那形成意见的能力……这一能力能给你精思熟虑、对于人的友爱、对于神的虔敬”。
“要以下述的两个念头安慰自己:“一个是:凡是与宇宙自然之道不相合的事物,绝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;另一个是:凡是与神及我内心神明相反的事,我绝不去做。”
“对于没有理性的生物,以及一切情况和客观事物,你要保持慷慨仁慈的态度,因为你有理性而他们没有。但是人是有理性的,所以更要以友爱的态度待他们。在任何时候都要求助于神。”
“作你灵魂主宰的理性,不可被肉体的任何活动所骚扰,无论其为愉快的或苦痛的。”
“凡合于自然之道的言行,你都要认为是值得做的……追随你自己的本性亦即宇宙之道,二者根本是同一条路。”
这就是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”的另一表述,正所谓“东海有圣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西海有圣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”。
“那不正当地行动的人也是在不虔诚地行动。因为既然宇宙本性为相互合作的目的造就了理性动物,要他们根据他们的应分彼此帮助,而不要相互损害,那么违反他意志的人,就显然对最高的神犯有不敬之罪”。
良知是神放置在人心中的指北针,它指引着我们,越过人世的艰阻;背离良知显然等于是背叛上帝。
马可·奥勒留认为:
一个人应该“永远要努力保持哲学所要把你熏陶成的典型,敬神而爱人;人生苦短,我们在世上可以收获的只有虔诚的性格与仁爱的行为”。
他告诫我们“不要怨命,要安贫知足,要慈爱、独立、节俭、严肃、谦逊”。
“如果你的畏惧不是因为你在某个时候必须结束生命,而是害怕你从未开始过合乎本性的生 活,那么你将是一个配得上产生你的宇宙的人。”
“请看下面这些是不是更为使人快乐;心胸高超、特立独行、朴素无华、慈悲为怀、生活圣洁;还有什么东西比智慧更能使人快乐?……”
要“任何事都不听从运气;除了理性之外,绝不仰仗任何东西”。
“你不能停止珍视其他许多东西吗?那么你便不能获得自由,也不能知足,也不能不被欲念所动。因为你必定是要充满了艳羡嫉妒之情,猜疑那些能夺去你这许多东西的人们;对于拥有你所珍视的东西的人们,你也不免要动阴谋邪念。简言之,一个人如果还需求那些东西,其心理必定不能和谐安宁,而且有时还要抱怨上天。但是如果你珍视你自己的心灵,则必然能怡然自得,与人无争,与天神和谐;换言之,感激上天的一切给予与安排,这才是你该珍视的!”
“在人的结构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友爱的原则。其次是不要屈服于身体的引诱。因为身体只是有理性者和理智活动确定自己范围的特殊场所;不要被感官或嗜欲的运动压倒,因为这两者都是动物的,而理智活动却要取得一种至高无上性,不允许自己被其他运动所凌驾”。
“哲学家说,每一灵魂都不由自主地偏离真理,因而也同样不由自主地偏离正义、节制、仁爱和诸如此类的品质。总是把这牢记在心是很有必要的,因为这样你就将对所有人更和蔼。”
斯多葛派强调忠于职守。奥勒留说:
在天亮的时候,如果你懒得起床,要随时作如是想:“我要起来,去做一个人的工作。”我生下就是为了做那工作的,我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做那工作的,那么现在就去做那工作又有什么可怨的呢?
人人都有天职,尽职尽责就是在追随神。
“我们都是想要完成一个目标的共同工作者……你自己是哪一类工作者?要由你自己决定。主宰宇宙的神明,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好好地利用你的,并且在共同工作者之间给你一个位置。但是要注意,不要成为克律西波斯所提起的那种猥琐而滑稽的剧中角色”。
奥勒留作为罗马皇帝,恪尽职守,他领导了四次军事行动,打垮了入侵的日耳曼部落,准备建立新的行省,可惜功败垂成、未竟全功。病死后,他的儿子康茂德转攻为守,与日耳曼人修和,埋下了祸根。
“哲学家说,如果你愿意宁静,那就请从事很少的事情……我们所说和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不必要的,一个人如果取消它们,他将有更多的闲暇和较少的不适……一个人不仅应该取消不必要的行为,而且应该丢弃不必要的思想”。
这句话非常值得咀嚼、回味。
“大道以多歧亡羊,学者以多方丧生”。华枝春满,天心月圆 ;广博之极,归于约简;绚烂之极,归于平淡。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”,得一者,万事毕。
“你管别人是怎样看你呢,只要你将以你的本性所欲的这种方式度过你的余生你就是满足的……你有过许多流浪的经验却在哪儿都没有找到幸福:在三段法中没有,在财富中没有,在名声中没有,在享乐中没有,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幸福。那么幸福在哪里?就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求的事情”。
尽人事,听天命,岂有他哉。
“用朴实、谦虚以及对与善和恶无关的事物的冷淡来装饰你自己。热爱人类,追随神灵。诗人说,法统治着一切,-—记住法统治着一切就足够了”。
法是隐秘的,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,需要我们细心体察。
“驱散幻想。不要受它们的牵引。把自己限制在当前”。
所谓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,“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愿乎其外也”。
“人们竭力追逐的一切是多么无价值啊,而对一个人来说,在提供给他的机会中展示出自己的正直、节制,忠实于神,并且非常朴实地这样做是多么贤明啊!”
这句话应该送给当下的大多数中国人。他们不知道活着就是考试,拼尽一生,竭力追逐的一切几乎都是泡影,毫无价值。
理想,不是逃避现实的理由;现实,就是逃避理想的理由吗?
他希望寿终正寝:“丢开对书本的渴望,你就能不抱怨着死去,而是欢乐、真诚地在衷心感谢神灵中死去”。
但也相信在必要时,一个人应该舍生取义:“一个毫不犹豫便会跻身于赴死者的高尚队伍的人,便是一个类似祭司和神之伺奉者的人,一个能够正确利用心中神性的人。”
事实上,杀身成仁者,几乎百分之百成为高级生命。
舍才能得,决非虚语。
自由平等是欧洲人世代相传的理念。时起时伏,时隐时现,终成滔滔江河。奥勒留像他的养父老安东尼皇帝一样:“他把自己视为与任何别的公民一样平等的公民”,告诫自己不要奢望“一切需要墙和幕的东西”。
结党营私、蝇营狗苟的某国官员,与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君主比较,恐怕是望尘莫及。
他说:“…所谓一个国家,即是根据个人平等与言论自由以制定一套法律,适用于所有的人;所谓君主,其最高理想乃是人民的自由。”
这是贤君。专制君主,却动辄作威作福、草菅人命。只有把权力的猛兽关进笼子,人民才会真正安全。
“大隐隐于市”,“心远地自偏”,斯多葛主义者把出世与入世更好地结合了起来,不像东方的隐士们,一味地逃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。
奥勒留说:“一般人隐居在乡间,在海边,在山上,你也曾最向往这样的生活。但这乃是最为庸俗的事,因为你随时可以退隐到你自己心里去”。
奥勒留力主宽恕,他说:
“理性的动物是互相依存的,忍受亦是正义的一部分。”
“别人的错误行为应该由他自己去处理。”“如果他做错事,是他作孽。也许他没有做错呢?”
吉本曾经指责,奥勒留过份的宽容完全超过了个人良好品德的限度。君主的道德与普通人还是应该有所不同。
“别人的错误行为使你震惊么?回想一下你自己有无同样的错误。”
“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”,“上不怨天,下不尤人”。奥勒留与中国古代的圣贤,可谓是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。
“对于那些容易发脾气冒犯人的人们,要随时准备和平相处,并且如果他们有意悔过迷途知返,要半路迎上去。”
奥勒留这样说,也是这样做的。
公元175年,叙利亚总督阿维第厄斯·卡希厄斯误以为奥勒留已死,举兵反叛,奥勒留就准备脱袍让位,弭兵息争。卡希厄斯被杀后,奥勒留闷闷不乐,叹息自己“失去了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”,他有意毁掉了一切有关叛乱的文件,以免牵连参与其中的人员。
他命令角斗士必须使用粗钝的剑,进行角斗。作为元首,他经常需要出席观看角斗、赛车比赛,无法拒绝。但他常在角斗场里看书,为此曾得罪了不少人(与中国君主不一样,罗马皇帝是不能完全罔顾民意的,他没有可能废止角斗)。
公元180年,奥勒留因染瘟疫病逝于潘诺尼亚的文都滂那(维也纳)军营。
历史公认,他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,欧洲历史上罕见的哲学王。
仁慈恺恻,智勇双全,文治蒸蒸,武功赫赫。与中国的哲学王——周文王或者可以颉颃上下,并驾齐驱(但《周易》是天书,玄妙莫测,《沉思录》无法与之相提并论)。
他用法律保护弱者,改善奴隶生活,普建慈善机关,救助罹灾百姓,深得罗马人民的爱戴。
随着他的去世,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,也杳如黄鹤,一去不再复返。
泰山其颓乎?哲人其萎乎?千载之下,犹有余哀!
马可·奥勒留死后,其子20岁的康茂德(Commodus)继位。
他冥顽不灵,放纵荒淫,任用奸佞,怠理政务,果于杀戮,终于在公元192年的最后一天,引来了杀身之祸。